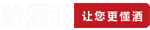艺术来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。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,他们的作品往往影射他们的生活,生活是艺术的物质银行,没有生活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作品。很多歌手二十多岁成名后,就没东西卖了,甚至靠毒品找灵感。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。这些人成名之后,有了钱,就没有了想要却不能的东西,失去了追求,终日迷失在琐碎和欲望中。自然,他们写不出好歌。就连他们写的歌都和大众的感受相去甚远,无法引起听众的共鸣,自然就没人要了。
本以为辞职后可以专心写作,现实中却打了自己一个耳光。因为我与生活脱节,除了姐姐,生活中没有其他人与我有交集,灵感枯竭。起初,我写了一部关于办公室恋情的都市小说。本来计划三个月写完10万字,结果花了半年才写完。其实10万字对我来说不算多。难的是故事细节的描述。比如我想写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是怎么因为深夜加班认识的,怎么约会的,被同事发现后心理变化如何.这些细节的描述可以营造出画面感。我经常闭着眼睛躺在床上,想象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,模拟他们的心理变化。但是因为离开工作太久,忘记了办公室的感觉,经常闭上眼睛一片空白。
我给这部小说起了个名字《羞月》,投给了某省级刊物,却被无情退回,连退稿建议都没有。我真的不希望半年的努力是这样的结果,然后投资了很多市级刊物和少数民族题材的杂志。过了差不多一个月,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,一个叫《风花雪月》的杂志编辑部给我发来邮件,说我的《羞月》写得很好,希望在爱情的细节上有更多的画面,以满足读者对其“成人小说”的需求,并承诺一旦收录,可以支付两万稿费,仍有机会成为他们。两万块钱不多,但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一方面,我急需为半年的辛苦找个说法;另一方面,我也需要改善我的生活。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。

小说《爱》关于细节的素材来源于我和方姐姐的真实故事。我把自己想象成男主,把妹妹方想象成二十五六岁的女主。我们俩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,她的工作站就在我的旁边。我在故事里写道:“有一天晚上,因为没有完成一份报告,我们加班到深夜。办公室突然停电了,房间里黑得可怕,但窗外蓝色的夜空浪漫地布满了星星。她说她怕黑,我就走过去拉着她的手说:“我们一起看星星吧!”她没有挣脱我的手,跟着我走到窗前,一起看着蓝色的星空。我站在她身后,轻轻抱住她,对着她的耳垂呼吸。她的眼睛依然凝视着远方,我能感觉到她鬓角的碎发在颤抖。我的手,像一条蛇,钻进扣子的缝隙里,寻找神秘美味的禁果……”,在这种场景下,应该是没有人能抵挡禁果的诱惑。背后的故事,自然是办公室里的男女之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我在小说里加了很多篇幅描述画面细节,各种时空场景都有,比如男主和女主一起去露营,一起在商场试衣间试衣服,他们一起去KTV唱歌.
《羞月》得到了《风花雪月》杂志编辑的认可。除了2万稿费,我还成了杂志签约写手。我需要定期定量输出一些稿件,按照每千字300元的价格拿稿酬。接下来的一年,我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男人和女人的故事。为了达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,每一个关键细节总是要占很大的篇幅,每一根头发,每一次呼吸都不放过。
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与社会隔绝了很久,素材库(生命)早已枯竭,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雷同。后来被杂志社取消了,退的稿子越来越多,精神越来越焦虑。我试图用酒精来激发灵感。我喝了一瓶白酒后,精神和肉体开始分离,肉体越来越重,精神却变得明亮,仿佛脱离了肉体的牢笼,以各种形态自由变换。有时候好像回到大学的时候,我们一起打游戏,一起疯。有时候我好像和一个女人躺在床上。她的皮肤温暖而光滑。我能感觉到她的每一个毛孔,却看不清她的脸。不管我怎么揉眼睛,都不管用。从她脸颊的轮廓来看,她有点像张、和周姐姐方。每当我沉醉在这种迷迷糊糊中,就会有一种思绪四溢的感觉,但这种感觉的尺度很难控制。太少达不到这种感觉,太多会导致我躺在床上睡着。就像王羲之一口气写下33,360,010-30,000一样,我也在纸上下了功夫。但每次醒来,我都对纸上的东西感到困惑,像是文字,更像是涂鸦。

因为连续喝酒熬夜,身体瘦得跟木乃伊一样,自然应付不了大姐的收租。甚至厌恶,潜意识里,男女之间的暧昧已经变成了一种血淋淋的,黏黏的,臭烘烘的东西,就像几百条蚯蚓互相拥抱,粘液里还有气泡。这些东西逐渐体现在我的作品里,把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描述成一种惩罚。故事中,男女主人经常遭受非人的折磨。比如女主被绑架,男主来英雄救美。绑匪让他们住在ML里,硬不起来就砍她。或者男主被恶魔附身,用某种恶心残忍的方式占据了女主。描述了女主醒着的时候躺在旁边的女主的复杂感受,恶心,恐惧,悲伤……都有。这些作品自然不符合编辑的口味,但我选择在酒精中发泄我所有的愤怒。
对于我拒绝“收房租”之事,房姐一开始并没说什么,只是让我注意身体,还经常贴心地给我做了一些好吃的菜,诸如红烧羊鞭、闷煮牛宝这类的大补的菜。为此,她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保温饭盒,盖子一开,香气扑鼻。有时候她会为我打扫屋子,帮我整理衣物,把喝完的酒瓶带到楼下垃圾箱扔掉。这一切让我有种错觉,以为自己是这个房子的男主人,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一切,甚至有时候我喝醉了酒会对她大呼小叫。有一天我还在睡梦中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声,睁开眼之后看到房姐张着嘴巴站在我的房间门口,看到我睁开眼她松了一口气,但仍然是一幅惊魂未定的样子。
“你刚才的样子,我还以为你死了,太吓人了。腿挂在床沿上,胸口塌陷,看不到一点起伏,整个身体骨瘦如柴、一身惨白,简直是一个吸毒过量致死的现场……”房姐拍了拍胸口,她今天没带好吃的过来,看我的眼神也少了那种爱慕,表情里多了一丝嫌弃,像饭菜里掉了苍蝇。
“房姐呀,我还困着呢?今天不想‘收房租’,你再让我睡一会行吗?”我一点不在意她说得吓人的场面,重新倒了下去打算继续睡觉。
“谁要跟你‘收房租’,你收拾一下找个时间搬走吧!这个房子我打算租给别人了。”说完她扭头就走了,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一声“砰”的关门声。
我以为房姐只是随便说说的,谁知道没过两天,两个彪形大汉开门冲了进来。他们让我现在就搬走,我说我不走,到外面没地方住。他们就一人抓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架起来扔到了楼下,接着将我的东西连踢带扔地堆在了垃圾桶旁边。两个大汉走后,我坐在垃圾桶旁边发呆。
半年没有离开这栋楼,此刻外面的环境对我来说有点陌生。太阳从东南方向刚刚升起,让这个秋天升起一丝暖意。斑鸠在树上嬉闹发出“咕咕”的叫声,它们很会伪装。远远地,只能看到树叶晃动,看不到一只斑鸠的身影。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从楼里出来,小孩蹦蹦跳跳,嘴里唱着“门前大桥下,游过一群鸭……”
我站起来,在一堆垃圾中找出钱包,再随便拿上一件外套,晃晃悠悠地离开了……